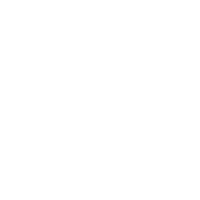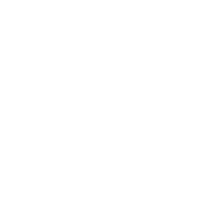人民法院报刊载北师大法学院本科生就“中间人罗某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的案例研讨
贾济东,张倩慧,钟琬群
编者按
诚邀全国各高校法学院师生及其他有兴趣的读者积极参与对以下案例的研讨,共同推动相关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深化发展。该案例案情虽简,但法律定性复杂,具有较高的学术讨论价值,涉及诈骗罪、侵占罪、行贿罪、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介绍贿赂罪等多种罪名,集中体现于一个看似简单的法律关系之中。2025年11月6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法学专业学生围绕新型职务犯罪的表现形态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探讨与交流。与会学生思维活跃,观点富有创见,展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相关研讨成果已由《人民法院报》以文字及视频形式刊发,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积极反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专业学生亦对该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思考,结合刑法理论前沿问题,运用创新性研究方法持续推进相关学术探讨。现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整理发布,敬请读者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济东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倩慧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钟琬群
2025年11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运用刑法新思维对“中间人截贿、获取感谢费的性质认定”在课堂上进行了热烈研讨。学生围绕下列案例进行了讨论,现将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案情:“吴某系私营企业主,其知道被告人罗某与国家工作人员张某系多年朋友,遂委托罗某说情,让张某关照某项目的审批。后罗某向张某请托,张某答应帮忙。罗某遂向吴某表示要送给张某300万元,吴某同意并向罗某付款。罗某将其中的200万元送给张某,另外100万元占为己有。后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吴某完成了审批。吴某为感谢罗某,事后送给罗某感谢费50万元”,讨论的是中间人罗某的行为的司法认定。
一、罗某撮合介绍行为应如何认定
陈寇认为,被告人罗某的行为首先构成受贿罪共犯,符合受贿罪共犯的构成要件,主体要件上,张某系国家工作人员,罗某虽非国家工作人员,但作为帮助犯,通过传递请托、转交贿赂款的行为配合张某实施受贿,符合共犯主体要求。主观要件上,罗某向张某转达吴某请托时,明确告知需“送钱”,二者就“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利”形成共同故意,且均明知张某的职务行为与财物具有对价关系。客观要件上,张某实施“利用职务便利审批项目”的实行行为,罗某实施了帮助行为,二者分工协作完成权钱交易。需特别说明:罗某截留100万元是共同受贿所得的内部分配行为,不影响共犯成立,共同受贿数额应认定为张某实际收受的200万元。
其次,被告人罗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要件上,罗某与张某系多年朋友,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主观要件上,罗某明知吴某支付50万元的目的是“感谢其促成张某为项目审批提供帮助”,而非“向张某追加行贿”,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该笔“中间人报酬”的故意。客观要件上,50万元感谢费是吴某在项目审批完成后支付的,与前期300万元贿赂款无关联,罗某收取该款项且未转交张某,本质是利用与张某的密切关系获取不正当利益,符合“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收受财物”的客观要件,应独立评价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综上所述,被告人罗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应数罪并罚,截留的100万元属于受贿罪共犯的违法所得,50万元感谢费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违法所得,均应没收。
王炳玺认为,该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罗某在明知吴某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情况下,向国家工作人员张某转达请托并转交贿赂款200万元,其行为在行贿人吴某与受贿人张某之间起到了沟通、撮合的作用。因而此行为涉及受贿罪共犯与介绍贿赂罪两种定性。首先此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按照共犯主体身份标准分类,共同受贿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共同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非公务性职权)之间共同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与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员之间共同收受贿赂。显然本案中罗某的行为应当在第三种情况下进行讨论;这类主体又分类为特定关系人和特定关系人之外的其他主体,不同主体认定受贿罪共犯的要件不同。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罗某是否属于“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基于此罪名的性质,这个共同利益应当为经济利益,而此案中罗某将100万元占为己有并收取50万元感谢费的行为并不为张某所知晓,因此在此方面无法认定具有“共同利益”。那么罗某属于特定关系人之外的其他主体,这类主体认定受贿罪共犯的要件为“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对于张某收取的200万元,罗某与张某有事先通谋,但是没有共同占有,因此其转达请托并转交贿赂款200万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共犯。
在排除了受贿罪共犯的认定后,罗某作为中间人,在行贿与受贿双方之间牵线搭桥、传递贿款,促使行贿受贿得以实现,且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符合介绍贿赂罪的构成要件。
丁文馨认为对中间人罗某的行为的认定首先应考虑是否构成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若难以认定为共犯的,可考虑介绍贿赂罪;在中间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时还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截取的钱款和收取的感谢费作为违法所得没收。第一,它严格遵循了刑法理论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贿赂犯罪中,最关键的是中间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通谋的行为。如果罗某与张某事前有约定,张某对罗某占为己有的100万元的行为知情或默许,那么罗某与张某就形成了一个受贿的共同犯罪体。反之,如果罗某是背着张某截留款项,张某对此并不知情,那么罗、张二人就缺乏共同受贿的故意,不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它灵活运用了刑法分则的罪名体系,当无法认定罗某与张某构成共犯时,刑法分则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更精准的选择。罗某利用与张某“系多年朋友”的密切关系,通过张某的职务行为为吴某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并因此收取了50万元的“感谢费”。罗某向吴某虚报行贿数额,骗取100万元的行为独立于贿赂犯罪本身,它侵犯的是吴某的财产所有权。第三,它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罗某在本案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他既是行贿的促成者,又是贿赂行为中的一环,也是利用张某影响力的获利者。总体而言,我们需要先确定核心的共犯关系,再评价其独立的欺诈与影响力交易行为。这样既能避免重复评价,又能防止评价不足,确保最终的法律制裁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罗某的全部罪行。
孙羽函认为,在当前反腐败刑事法治体系不断精细化的背景下,本案关于罗某行为的定性争议较大:罗某既与行贿人吴某存在明确的请托关系,又通过虚构事实截留部分款项,同时还在事后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收受“感谢费”。前边有同学主张将罗某评价为行贿罪的共犯,强调罗某属于贿赂行为链条的一部分。但其中比较容易忽略的是罗某主观目的与动机。罗某不仅“传话”,更主动虚构事实、诱使吴某支付远超必要的金额,其动机已从单纯促成请托转向非法占有。此外,事后罗某单独收受的50万元感谢费也明显超出了“共同行贿行为”的范畴。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应当对罗某分别构成行贿罪、诈骗罪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数罪并罚”。具体来看,罗某与吴某最初的请托行为属于典型的向国家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其共同实施的行为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但在金额问题上,罗某虚构了“张某需收受300万元”的事实,诱使吴某在错误认识下给付财物,并最终将其中100万元据为己有,“被害人自身违法”并不阻却诈骗的成立,只要其处分财产是基于错误认识即可。至于事后收取的50万元,我认为这构成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此时的利益交换不再涉及行贿过程,而是罗某基于与张某的密切关系,通过影响张某的职务行为为吴某谋利,从而索取、收受财物。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规定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的核心在于其是否能够“凭关系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综合前面所讲,对罗某实行数罪并罚,即将其行为拆分为三个犯罪行为分别处理:首先,他与吴某共同实施的对张某的请托行为,成立行贿罪;其次,他通过虚构事实侵吞行贿款项中的100万元,构成诈骗罪;最后,他利用与张某的关系,在事后收受的50万元,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徐艺萌认为,罗某的行为构成行贿罪共犯与侵占罪。罗某明知吴某送钱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仍主动提出代为“打点”,并亲自将200万元交给张某,从而促成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吴某审批项目。罗某在主观上与吴某具有共同的行贿故意,客观上共同实施了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符合行贿罪共犯的构成要件。同时,罗某将吴某委托代转的300万元中私自截留100万元,占为己有,其在取得时系合法占有,但主观上转化为非法占有并擅自处分,已构成侵占罪。至于其他罪名,应予排除。罗某并非以“影响力”为交易对象,而是以“金钱行贿”为目的,且最后的50万元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是以影响力为条件完成的,而是违法所得的一笔感谢款。故不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非单纯牵线撮合,而是亲自实施交付,不构成介绍贿赂罪;且吴某基于信任委托,并非因受骗处分财产,不具备诈骗罪的欺骗结构。综上,罗某在本案中兼具“行贿共犯”和“侵占财物”的双重违法性,应依数罪并罚原则定罪处罚。
张欣玥认为中间人罗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罗某在本案中占有这100万元的行为,吴某与张某均不知情,因此罗某向吴某表示的“要送给张某300万元”系虚构事实,使吴某产生了“300万元是交给张某的作为其完成请托事项的必要款项”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这一错误认识对300万元钱款作出了交付财产的处分行为,且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获得了其中的100万元,符合构成要件,应认定中间人罗某构成诈骗罪。
本案中罗某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接受吴某的委托,利用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张某的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请求张某关照吴某相关项目的审批,为请托人吴某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凭借其履行的请托行为从吴某处获取了50万元感谢费,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构成要件,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综上,我认为本案中犯罪中间人罗某构成诈骗罪,诈骗财物100万元;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涉案财物50万元。
赵一萌认为,罗某与吴某构成行贿罪的共同犯罪,犯罪数额是300万元。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吴某实施了欺骗行为,导致吴某产生错误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财物,罗某诈骗罪的数额是100万元。张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受贿罪,罗某将200万元送给张某,构成受贿罪的帮助犯,受贿罪的犯罪数额为200万元。罗某既构成行贿罪的共同犯罪,又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两者想象竞合。吴某事后送给罗某感谢费50万元,罗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数额为50万元。综上,罗某构成行贿罪和受贿罪的想象竞合,诈骗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赵一萌认为罗某不构成介绍贿赂罪,因为介绍贿赂罪更加强调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沟通,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而在这个案件中,罗某明显起到了实质性作用,作为行贿和受贿的主体参与了受贿和行贿的过程,而不是站在中立第三者的立场,因此不构成介绍贿赂罪。
郑璨认为,该行为构成行贿罪共犯以及诈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数罪并罚。行贿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罗某转交的200万元,正是对这一法益的直接冲击。罗某本身是一个介绍贿赂的行为,但是由于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收取较大数额钱款,进而转化为行贿罪的共犯。而诈骗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财产所有权”。罗某骗取100万元,直接侵害了吴某的个人财产,这与国家职务行为廉洁性无关。而上一个同学提到的认为吴某自身作为犯罪者,将其认定为诈骗不利于社会公正价值的倡导。我对此并不认同,即便吴某自身犯罪,他的合法权益也受法律的保护,并不能因为他的身份而有所差异。
郑金洹认为,200万元行贿款项的定性为吴某和罗某行贿罪共犯,罗某受吴某委托,将200万元交付国家工作人员张某,双方均明确“以钱换权”的行贿意图——吴某希望通过款项获取审批便利,罗某协助完成款项交付以促成交易,张某接受款项后利用职务便利为吴某办理审批。该行为中,罗某与吴某存在共同行贿的故意,且实施了协助交付行贿款的行为,构成行贿罪共犯;张某接受款项并为他人谋利,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为200万元。
罗某的行为不应笼统认定为介绍贿赂罪,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介绍贿赂罪本质是在行贿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承担“牵线搭桥”的媒介角色,以“单纯媒介行为”为前提,无实质参与行贿款项控制或利益分配的行为。而本案中罗某不仅为吴某联络国家工作人员张某,更实际掌控吴某交付的300万元行贿款项,自主决定款项分配,且在项目审批完成后收取50万元感谢费。其行为已超越“介绍”的范畴,深度参与行贿的核心环节,符合行贿共犯或受贿共犯的行为特征,若仅以介绍贿赂罪评价,明显割裂了行为与犯罪本质的关联。
二、罗某截留100万元行为定性时的观点交锋
陈寇认为,罗某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和侵占罪,分别进行了排除分析。首先,诈骗罪的主观要件要求行为人具有“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故意”,而本案中罗某虽截留100万元,主观目的是“截留部分贿赂款”,与诈骗罪的主观故意本质不同。其次,吴某支付300万元的目的“通过行贿获取项目审批便利”已实现,吴某并未因罗某的行为陷入错误认识。最后,罗某截留的100万元是“贿赂款”,属于受贿罪共犯的违法所得;而诈骗罪的对象是“被害人的合法财物”,二者性质完全不同,进一步排除诈骗罪的适用。对于侵占罪,首先,侵占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合法财物的故意”,且该故意基于对合法保管关系的违背。本案中,罗某截留100万元的故意,源于对自身“影响力”的利用,而非对普通民事保管义务的违背。其次,侵占罪的客观前提是行为人“合法持有”他人财物,而本案中,吴某交付300万元给罗某,是委托其用于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属于非法委托,罗某对该款项的持有缺乏合法依据。最后,侵占罪保护的是权利人合法的财产所有权,而罗某截留的100万元属于用于行贿的“不法原因给付物”,吴某因自身具有行贿的非法目的,对该款项丧失了合法的返还请求权,该款项并非侵占罪所保护的合法财物范畴。
李晗羽赞同陈寇同学的观点,支持罗某不构成诈骗罪,从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论证。首先,诈骗罪的核心逻辑链条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该认识错误而处分财物→行为人因此取得财物”。但是,罗某首先不具有诈骗罪意义上的“欺骗行为”。吴某的核心诉求在于借助特殊关系请托张某,以实现不正当利益。支付300万元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行贿换取张某的职务便利,而非单纯要求将钱足额转交张某本人。从事实来看,罗某实施了帮吴某向张某请托的行为,促成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完成项目审批,吴某的核心请托需求已得到满足。因此,无法将罗某的行为定性为欺骗行为。其次,吴某不存在“认识错误”。本案中,吴某关注的核心点始终是自己请托的项目审批能否完成,而非支付的请托费是否全额转交。换言之,在能够实现请托目的的前提下,无论是支付给张某200万元、300万元或其他合理数额,吴某对此均有概括的容忍度。
其次,诈骗罪的主观方面需要行为人直接故意,且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罗某显然不符合这一核心要件。从中间人的一般认知来看,罗某行为的整体意图为通过自身与张某的特殊关系,为吴某促成项目审批的请托事项,进而获取相应的报酬,而非通过欺骗手段骗取吴某的财物。截留100万元的主观目的并非“非法占有”,而是其帮助吴某联络国家工作人员、推动请托事项落地所应得的“辛苦费。最后,诈骗罪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本案中,罗某转交给张某的200万元已被纳入贪污贿赂犯罪的评价范畴,而案涉100万元的产生,同样根植于中间人罗某与国家工作人员张某的密切关系,且其目的仍是请托国家工作人员促成项目审批。究其本质,案涉100万元与200万元均指向对国家廉政制度和职务廉洁性的侵害,侵害的是相同的法益。
马艺萌认为,重点讨论本案罗某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认为罗某截留100万元行贿款、收取50万元感谢费的行为始终围绕贿赂犯罪展开,与诈骗罪的构成逻辑存在根本差异。从诈骗罪虚构核心事实的要件来看,案例中罗某并未虚构与吴某财产处分直接相关的关键事实。吴某的核心诉求是通过贿赂张某获取项目审批,罗某不仅没有虚构需要向张某行贿这一前提,更实际完成了请托,促成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审批项目,吴某的行贿目的已完全实现。罗某并未虚构张某会提供帮助的承诺,也未编造必须支付300万元才能获批的虚假条件。从陷入错误认识的要件来看,吴某自始明知支付300万元的性质是行贿,明知钱款的用途是换取张某的职务便利,其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是基于非法目的的主动选择,而非因误导产生认知偏差。即便吴某知晓罗某仅向张某转交200万元,只要项目能顺利审批,其仍会同意支付相应钱款。从财产处分与错误认识的因果关系来看,吴某支付300万元的直接动因是获取项目审批利益,而非相信罗某所说的300万元数额。这意味着,吴某的财产处分与罗某的截留行为无直接关联,更不是因被欺骗而作出的选择,完全断裂了诈骗罪要求的因果链条。
孙羽函认为,在金额问题上,罗某虚构了“张某需收受300万元”的事实,诱使吴某在错误认识下给付财物,并最终将其中100万元据为己有,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逻辑。“被害人自身违法”并不阻却诈骗的成立,只要其处分财产是基于错误认识即可。罗某截留100万元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宋洁认为,罗某截留100万元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排除侵占罪。罗某构成侵占罪的核心误区,在于将“委托关系的存在”等同于“持有财物的合法性”。但本案中,委托关系的建立本身就基于罗某的欺骗行为——吴某是因相信“300万元全部用于行贿”才交付款项,而非概括委托罗某“自主处置款项”。罗某截留的100万元,自始就不属于“代为保管的合法财物”,而是通过欺骗直接骗取的财物,这与“合法持有后侵吞”的侵占罪本质完全不同。综上,罗某通过虚构贿赂数额、隐瞒截留事实的方式,骗取吴某100万元,完全符合诈骗罪“欺骗行为——错误认识——处分财产——非法占有”的完整逻辑链,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王炳玺认为,截留100万元构成诈骗罪,排除侵占罪,理由在于罗某向请托人吴某谎称需要300万元用于向国家工作人员张某行贿,但实际仅将200万元交给张某,自己截留了100万元。罗某具有非法占有该100万元的主观故意,行为符合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构成要件,使得吴某基于错误认识(认为300万元均用于行贿)处分了财产,罗某因此非法占有了100万元。此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侵占罪以行为人合法持有为前提,而本案中,吴某交付300万元的目的是用于行贿,该款项的性质是犯罪工具(贿赂款),不属于法律上受保护的“他人财物”。因此,罗某截留该款项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赵一萌认为,罗某对自己占有的100万元不构成侵占罪,因为侵占罪是将他人所有自己占有的东西变成自己所有的,他人应该享有一个合法的返还请求权,而此时100万元作为赃款,我国刑法是不保护赃款的,因此吴某此时对100万元没有返还请求权,因此不构成侵占罪。
郑金洹认为,100万元截留款的定性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罗某与张某存在“多年朋友关系”,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吴某将100万元支付给罗某,核心目的仍是“通过罗某的影响力获取张某的职务关照”,符合“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且因款项已实际交付,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应的,罗某接受该100万元,利用与张某的特殊关系为吴某谋利,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从罗某的主观层面看,其截留款项时认为该部分是促成交易的应得报酬,而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财物,缺乏财产犯罪的主观故意,因此罗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侵占等财产犯罪。
三、吴某事后送给罗某感谢费50万元的行为如何认定
王炳玺认为,中间人罗某收取感谢费50万元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罗某与张某是“多年朋友”,关系密切。他通过张某的职权行为为请托人吴某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事后,他利用这种影响力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了吴某数额巨大的“感谢费”。这个行为独立于之前的介绍贿赂行为,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孙羽函认为,事后收取的50万元,构成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此时的利益交换不再涉及行贿过程,而是罗某基于与张某的密切关系,通过影响张某的职务行为为吴某谋利,从而索取、收受财物。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可以看出,这属于典型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的核心并不在于行为人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在于其是否能够“凭关系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罗某与张某的关系密切、确能促成吴某获利,所以有充足依据认定这一项罪名。
郑金洹认为,中间人罗某收取50万元感谢费的定性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笔款项是吴某在项目审批完成后,为感谢罗某“促成交易”而支付的对价。从本质上看,罗某能够获取感谢费,仍是基于其与张某的特殊关系。该行为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要件,故罗某收取50万元感谢费的行为,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吴某对应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阅读次数: